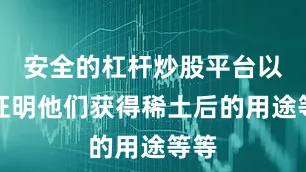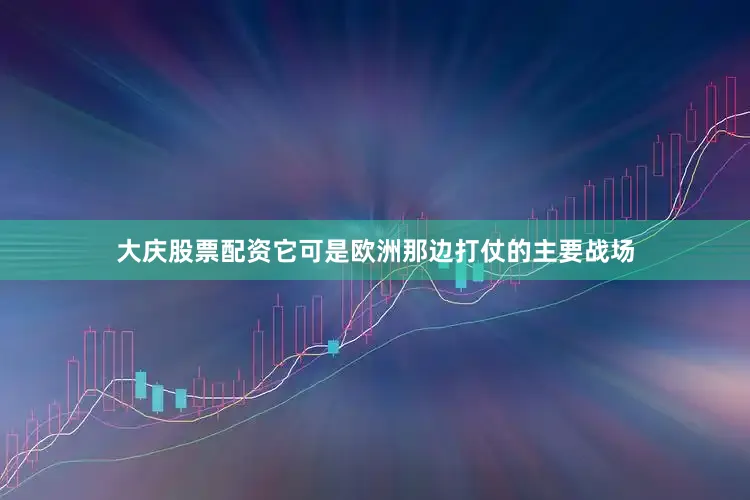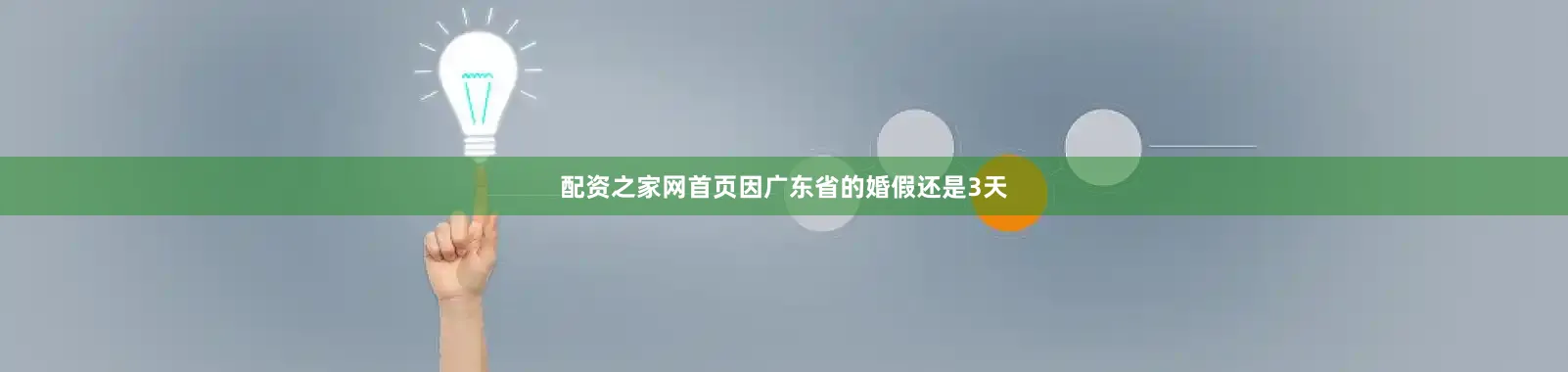他诞生于一个文人世家,堪称全球学术界的翘楚。若他选择留在美国,无疑将享受到优渥的生活条件。然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归国,于浩瀚的戈壁滩上默默耕耘,为国家默默奉献。他的身影与名字,在岁月的长河中鲜为人知,但他对新中国国防事业的贡献,却是无比巨大。他就是邓稼先。
少年有志
1924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即公历6月25日,安徽省怀宁县城郊的一座名为“铁砚山房”(民间又称“邓家大屋”)的文人世家迎来了新的生命。这一日,邓以蛰与王淑蠲夫妇喜不自胜,因为在此前,他们已育有两位女儿——邓仲先、邓茂先,而眼前的这位则是邓家首位男丁。在喜悦之余,他们为这位新生命赐予了名字——邓稼先。邓以蛰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王淑蠲亦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夫妇俩对邓稼先寄予厚望,期望他自幼勤奋好学,日后成为一名有学问的人。
邓稼先不负父母所望,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三岁四岁之际,已能辨识众多文字,熟记多篇古典文学佳作。彼时,邓家已迁至北京,这座城市早已涌现出众多新式学堂,涵盖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鉴于邓稼先年纪轻轻便已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天赋,且读书识字颇丰,邓家父母经过商议,决定在1929年9月,即邓稼先五岁稍过之时,将他送往北平的武定侯小学就读。
在学校中,尽管邓稼先年纪尚轻,他的表现却格外出众。他不仅在学业上名列前茅,与人交往亦谦逊有礼,那股孜孜不倦的读书热情,彰显了他幼小心灵中强烈的进取之心。老师和同学们无不对这个年纪尚幼的孩子投以赞许的目光。
◆铁砚山房外景。
1936年,年仅十二岁的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并顺利进入初中二年级。
崇德中学以其理科实力著称。在这里,邓稼先度过了三年的学习时光,为他的英文、数学和物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成为他日后享誉全球的关键起点。在崇德中学,邓稼先结识了高他两班的杨振宁,两人在家庭背景、少年时期的聪慧以及科学救国的抱负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也让他们成为了挚友。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友谊历经数十年,直至邓稼先的离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一起合办,是为西南联大。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原打算随校迁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一家人也迁到昆明去,但他偏偏在此时患上了重病。无法,邓稼先一家只好滞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在日寇占领下生活,邓氏一家人饱尝亡国奴之苦,也激发了少年邓稼先的爱国情怀。
1941年,邓稼先历经辗转,自北平抵达昆明,投身于西南联合大学,专攻物理。他师从王竹溪、郑华炽等知名教授。西南联大汇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的师资力量,加之其在抗日战争中迁校建校的特殊背景,以及学校对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视和教授们的积极引领,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学术水平最高、抗战氛围最浓厚的高等学府。邓稼先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在此度过了四年的学习生涯,既沐浴在严谨治学的风气之中,又深受爱国情怀的滋养,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青年。这段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经历,他终身铭记于心。
偶然间,邓稼先在西南联大重逢了杨振宁,两人同校。彼时,杨振宁正就读于物理系研究生班,年级比邓稼先高一级。在这所名校中,他们的友谊得以延续,关系愈发深厚。

◆西南联大校门。
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读书,学习科学知识,是为了未来能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他已经将实现科技强国的愿望与国家现实紧密相连,将个人事业与民族兴衰融为一体。这位成绩优异、政治上积极进取、在抗日救亡的呐喊声中成长的青年,高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踏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娃娃博士”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让21岁的邓稼先首次体会到了扬眉吐气的喜悦。正是在同一个月,他完成了大学学业,伴随着胜利的号角,他找到了投身国家重建和社会振兴的第一份职业。当年9月,他登上了昆明文正中学的讲台,担任数学教师。邓稼先在教授数学时所展现的才华,迅速在昆明市各中学间传为佳话。培文中学随后将他调去担任数学教师。1946年1月,22岁的邓稼先再次来到昆明,在培文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因战争而滞后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急需大量人才。尽管邓稼先身处昆明,但他很快引起了北平复办的北京大学的高度关注。同年6月,邓稼先重返北平,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尽管他在昆明的两所中学任教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为他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为他日后为新中国培养科学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教于北京的邓稼先教授,不仅持续深耕学术领域,亦在学生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曾任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的主席。在北大,他迅速邂逅了爱情。在担任一年级物理课程的助教期间,他与1946年考入北京的许鹿希相识,两人一见倾心,坠入爱河。许鹿希,系五四运动杰出的学生领袖、日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德珩先生思想开明,对女儿的教育亦颇为重视,使得许鹿希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既思想前卫,又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从相恋到婚后几十年共同生活的岁月里,许鹿希始终默默支持邓稼先为国家献身,她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深深敬意。这将是后续的故事。

◆邓稼先
在北京大学执教的邓稼先,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在北大授课得心应手,未来一片光明。然而,怀揣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的邓稼先,并未因此而满足。他的志向远大,渴望前往科学水平更为卓越的美国深造,以获取更为先进的知识,待学成归来后,报效祖国。基于此考量,1947年,他参加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并一举考中。同年,他收到了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次年秋季,邓稼先远涉重洋,抵达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继续深造。彼时,他年仅24岁。
在普渡大学的研究生院中,邓稼先以其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而著称。他的刻苦钻研换来了卓越的学术成绩。在美国求学仅两年之余,凭借其卓越的学习成绩,他迅速完成了所有学分。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成功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荣获该校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此时,年仅26岁的他被誉为“娃娃博士”。
“今日你得以饱餐,还记得当年你在美留学时,常常饥肠辘辘的情形吗?”邓稼先亦不禁点头,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当时,他并无奖学金可依,就餐时不敢随心所欲,只能量力而行。曾有一段时日,他与洪朝生(后于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共居于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之中。一次,两人外出用餐,两份牛排被端上桌后,邓稼先端详片刻,对洪朝生说:“我的这份较小,你的那一份较大。”于是,洪朝生便慷慨地将自己的那块牛排让给了邓稼先。提及这些往事,杨先生与邓稼先不禁相视而笑。
勤奋的科学家
邓稼先的卓越贡献,很快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他们意图通过提供更为优越的科研与生活条件,将他留在美国。即便是他的恩师和同窗好友,也纷纷劝说他留下。然而,怀揣着对祖国深沉眷恋与忠诚的邓稼先,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美国的优渥生活与工作环境,选择返回祖国。1950年8月29日,正值他获得博士学位仅仅9天之际,他便踏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重返那个当时尚处于一穷二白状态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处于恢复与建设的关键阶段,亟需大量的科技人才。邓稼先学成归国后,在我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对他的回归给予了高度重视。同年九月,便将他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一职,专注于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金秋十月,北京外交机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款待了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归国科研精英。席间,有人好奇地询问邓稼先:“您从美国归来,都带回了些什么?”邓稼先幽默地回应:“我给父亲带回了几双国内尚无法生产的尼龙袜子,以及满脑子的原子核研究成果。”他的回答引得在场嘉宾纷纷捧腹。1951年,年仅27岁的邓稼先正式加入了九三学社。
归国后,邓稼先全身心投入科研事业。在中国科学院,他堪称最为勤奋的科研工作者之一。为了深入探究科学奥秘,他几乎到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解决科学难题的过程中,他广泛查阅资料,反复进行演算。在那个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我国尚未拥有电子计算机,邓稼先为了攻克一个难题,常常需要在纸上用笔进行大量的演算。在演算过程中,他必须高度集中精力,不容许有丝毫的分心。因为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错误,往往需要将所有的演算推倒重来。邓稼先在科研楼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一个个科研难题在他的努力下得以解决,而他办公室里的演算纸张堆积如山。
于研究所中,邓稼先堪称出入图书馆频率最高的学者之一。自归国伊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便留意到,频繁查阅资料者非邓稼先莫属,他总是最早踏入馆门,亦是最晚离去的身影。
岁月如梭,历经八载春秋更迭,邓稼先全神贯注投身于原子核理论的研究,硕果累累,成果斐然。1952年,他荣获晋升,成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年仅28岁。在当时的中国,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研职称者寥寥无几,邓稼先已然成为国内较为年轻的高级科研人才。这位青年才俊,与恩师王淦昌教授及彭桓武教授一道,投身于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共同开启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崭新篇章。

◆邓稼先和许鹿希。
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爱情持续绽放。许德珩对邓稼先亦颇为赏识。1953年,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举行了一场简约的婚礼。婚后初期,他们的生活过得颇为安定。1954年,他们的女儿典典(邓志典)降临人世。1956年,又迎来了儿子平平(邓志平)的出生。一家四口,其乐融融。邓稼先在政治生涯上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组织上对他的才能和贡献给予了高度关注。同年,年仅30岁的他荣获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的职位。1956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邓稼先亦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1956年,他携手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同仁,在《物理学报》上陆续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学术论文,这些成果为我国核理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使邓稼先成为我国核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贡献中国核工业
邓稼先的宁静生活与专注科研并未长久。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中国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研制出原子弹与氢弹。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调动人才,集中精力研制核武器。对于核理论颇有深造的邓稼先,自然进入了党中央的视野。1957年8月,年仅33岁的邓稼先被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该研究院属保密单位,其成员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邓稼先更是如此。然而,他在上任之初,尚能与家人同住,并与其他业务圈同仁交往。随着我国核研究的深入开展,相关部门决定将一批高级专家集中起来,在极度保密的环境下全力攻关。邓稼先便成为了这些高级专家之一。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亲自与邓稼先谈话,表示国家即将发起一项名为“大炮仗”的重要行动,并询问他是否愿意投身其中,这是一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回家后仅向妻子透露自己将“调动工作”,无法再兼顾家庭与孩子,通讯也将变得困难。从小接受爱国思想教育的妻子深知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对国家意义重大,毫不犹豫地表示全力支持。1958年10月,邓稼先告别了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与众多科学家一同投身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他们来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明媚的高粱地,隐姓埋名。随后,他们又转战戈壁滩。邓稼先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从那以后,熟悉他的人再也无法联系到他,科研杂志上亦不见他的名字,公开场合亦鲜少见到他的身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邓稼先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了近三十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埋藏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
起初,邓稼先与众位科学家聚首一堂,精心选拔了一批青年才俊,搜集了俄文资料及原子弹模型,意图接受苏联专家的指导,以期直接掌握核技术。然而,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急剧恶化,以赫鲁晓夫为领导的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协议,撤回了所有专家。我国期望直接从苏联汲取核技术知识的愿望,就此破灭。党中央果断决策,我国必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用八年时间研制出原子弹”,并号召我国科学家传承艰苦奋斗、独立探索的精神,从头开始,依靠我国的力量掌握核技术。邓稼先毫不犹豫地拥护这一中央决策,自此全身心投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核技术研究工作中。他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仅23岁的由28名应届毕业生组成的研究团队,踏上了探索原子王国的征程。在资料匮乏、试验条件艰苦的条件下,邓稼先肩负起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担。为了确保原子弹设计工作的领先地位,他指导大家刻苦钻研理论知识,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为团队成员推荐了一系列书籍和资料,坚信这些都是揭开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指南。鉴于资料均为外文且仅有孤本,邓稼先只得组织大家轮流朗读、翻译,并夜以继日地印刷。

◆邓稼先在工作。
“唉,一个太阳实在是不足够啊!”意在强调,我们必须将一日当两天来用。在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中,有一个关键参数——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需达到的大气压数值,对揭示原子弹原理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邓稼先带领青年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轮班计算,运用特性线法取得了与苏联专家结论截然不同的突破性成果。该结论最终得到从苏联归国的物理学家周光召从物理学角度的科学验证。邓稼先严谨的计算推翻了苏联人的原有结论,成功解决了关乎我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赞誉道,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这不仅是他指导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更具有深远的应用价值。
后续事实验证了邓稼先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这无疑是他对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领域所做出的最为关键性的贡献。
“这是什么玩法,竟还做起儿时的游戏。”即便如此,邓稼先亦深知时间宝贵,在短暂十分钟的游戏后,便迅速回归紧张的工作状态。
1962年9月11日,经罗瑞卿亲自审阅,二机部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名为“两年规划”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力争在1964年,最迟至1965年上半年成功引爆我国首颗原子弹。罗瑞卿在阐述此目标时,语气中透露出坚定与自信,这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邓稼先及其团队已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核武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二月,邓稼先赴华北某地,投身于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并亲自指导。在那里,他度过了长达七个月的时光,日夜坚守,辛勤工作,每日工作量超过十个小时。即便饥肠辘辘,他也只是简单地啃上一口馒头充饥;若是疲惫不堪,便在试验基地临时搭建的透风棚子里披上外衣稍作休息。凭借着这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他们最终实现了模拟试验的圆满成功,并研制出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到了1964年十月,邓稼先最终签署了我国首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十月的十六日,十五时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那一刻,邓稼先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在核武器研究领域,邓稼先肩负重任,领导团队深入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以及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成功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并亲自指导了核试验中的爆轰模拟实验。正当邓稼先及其团队致力于原子弹研究之际,1963年9月,聂荣臻元帅下达命令,指派邓稼先与于敏率领原班人马,继续深化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研究,同时肩负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重任。邓稼先再次集结力量,积极探索氢弹的设计原理,明确技术路径。面对这一艰巨任务,邓稼先亲自挂帅,带领科技人员全力以赴,历经一年的辛勤耕耘,终于迎来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与实验的重大突破。
邓稼先与周光召共同撰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堪称核武器理论设计领域的奠基性巨著。该书汇聚了百位科学家的智慧结晶,不仅对后续的理论设计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更成为了科研人员入门的必读教科书。在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上,邓稼先同样贡献卓著。为了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他还精心编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多门讲义。即便后来身兼院长重任,他仍利用业余时间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教材,为科研事业倾注了无尽的热情与智慧。
在逆境中的奇迹
1966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后,中央作出决策,确保负责国家核武器研发的基地与人员免受波及。鉴于这些单位实行军事管制,邓稼先所在的机构及其本人自“文革”伊始便未遭受冲击。正得益于这一层保护,邓稼先及其同在核武器研制领域的同事们得以专心致志,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就。到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加剧,核武器试验基地以及科研人员亦未能幸免于难。1971年,这场狂潮亦席卷至第九研究院及其试验基地。院内部部分人士成立了造反组织,着手对科研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进行批斗。造反派迅速分化为两派,他们在激烈的争吵与冲突中,竞相对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进行批斗。在这种形势下,众多在研制中国核武器过程中贡献卓著、功勋显赫的科学家遭受了不白之冤,受到了打压,邓稼先、于敏、胡思得等人均被集中至青海基地,遭受批斗之苦。
部分造反派在批斗过程中,竟勒令科学家们交出核武器研究的核心数据,此举令身处困境的邓稼先承受了极大的考验。面对批斗,邓稼先深知,若此刻违心言辞,泄露科研机密,将给我国核武器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尽管处境险恶,他仍坚韧不拔,与同行科学家们携手,坚决保守重要科研成果的秘密,未曾透露分毫。

当邓稼先等人面临困境之际,1971年,国际知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响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从纽约途经巴黎抵达上海,对中国展开访问。抵达后,接待人员询问他希望会见哪些人,杨振宁随即列出了一份名单,首位便是邓稼先。名单迅速从上海传至北京,呈递至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恩来立刻下令,务必尽快召回邓稼先至北京与杨振宁会面。中央办公厅以电报形式直接致青海基地,指明要求邓稼先返回北京。得知此电报后,造反派不敢再对邓稼先进行批斗,转而对他露出了笑脸。邓稼先返回北京后,造反派对他态度大变,变得非常客气。自此,邓稼先在基地的暗淡生活宣告终结。
“这封简短的信件让我深受感动,一时泪眼朦胧,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理妆容。”杨振宁认为,正是一群敢于奉献的知识分子,使得中国挺起了坚实的民族脊梁。
遵照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关怀并重用邓稼先等科学家,邓稼先在卸任不久后,便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支持下,依然执掌科研工作。自此,他致力于保障科研院所与试验基地的稳定。邓稼先的贡献卓越,个人魅力非凡,使得他在九院和基地内都享有崇高的声望。凭借这股声望,他成功说服了分裂为两派的造反组织,确保了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得益于周恩来的悉心庇护,以及邓稼先等同仁的辛勤付出,即便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九院与试验基地亦然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科研工作未曾停歇,反而在逆境中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
1972年,邓稼先同志受组织委派,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一职。当年,他正值48岁盛年。
无私奉献
邓稼先初涉我国核武器研制之时,恰逢我国经历的三年艰难时期。尽管尖端科研人员享有相对较高的粮食配额,但由于副食和油水的匮乏,他们仍常感腹中空空,却依然坚守岗位。邓稼先得以从岳父那里获得一些粮票的支持,他用这些珍贵的粮票购得许多饼干,并与并肩作战的同事们共享。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他们依然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精神高度集中。因为在进行“粗估”参数时,需要依靠敏锐的物理直觉;在昼夜不息的筹划计算中,需要具备深邃的数学洞察力;在决策方案时,则需展现出勇往直前的胆量和稳健的判断力。
邓稼先不仅日复一日地在高度保密的科研机构中投入紧张的科研工作,而且频繁深入人迹罕至的辽阔戈壁滩,亲自指导各项试验。在这片连飞鸟亦鲜少驻足的荒凉之地,他度过了无数个被烈日炙烤的四五十度高温夏日,也熬过了无数个气温跌至零下三十度,遭受狂风肆虐与沙尘侵袭的严冬,孤独地生活在试验场长达十年之久。他十五次勇敢地直面核辐射的风险,亲自领导核试验,亲临现场,积累了大量核试验的宝贵第一手资料。每次试验结束后,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第一个冲到现场采集样本,以验证试验效果。最为紧张的是,他同时肩负着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任务。他与于敏共同确立了“邓—于方案”,这一方案对于两弹的相继成功研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以及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实现了两弹研制间隔时间最短的壮举,远远超越了法国的8年、美国的7年和苏联的10年。中国因此创造了世界上两弹研制间隔时间最短的辉煌奇迹。
戈壁草原尽踏遍。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战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淡泊名利。
许国威壮山河。
功勋泽人间。
邓稼先以其低调务实的敬业精神著称,而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又与世隔绝,因此,许多关于他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直至他离世方才为人所知。

1979年,邓稼先(左图)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浩瀚戈壁滩上,与赵敬璞共同留下了珍贵合影,彼时二人寻回了一枚未爆的核武器弹头。
“你们尚年轻,不能冒险!”就这样,他带着病痛,在基地坚持工作了许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红云映九霄。
核力撼地动。
二十年来攀登后,
轻舟已过桥。
“我不能走。”直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他方才与众人一同返回休息。
1985年,邓稼先的病情已至危重,组织上毅然决定强制安排他入院接受治疗,这才使他得以入住北京的一家医院。卧病在床之际,他神色平静地感慨:“我预料到这一天终将到来,却未曾想到它会来得如此迅速。”临终之前,他依旧心系祖国战略武器的进步。即便身体极度衰弱,每次挥笔书写都需承受极大的体力负担,汗如雨下,他仍与于敏共同探讨我国武器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写下关乎国家未来的文字。最终,他与于敏联名,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邓稼先以生命之火,向祖国献上了无尽的赤诚。
邓稼先的癌细胞已广泛扩散,他内心深处亦深知,自己正接近生命的尾声。在此艰难时刻,他仅有一个愿望:在国庆佳节之际,能一睹天安门的风采。在有关领导干部和医务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凝视着城楼上那庄严的国徽,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多么渴望能再活几年,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党和政府竭尽全力挽救邓稼先的生命,于1985年8月为他实施了直肠癌切除手术。次年3月,他再次接受了手术,5月又进行了第三次手术。同时,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邓稼先给予了特别的荣誉和关怀。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亲自到医院为他颁发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组织上还为他配备了专车。然而,邓稼先这位思想境界高尚的科学家,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谦逊和谨慎的品格,并不愿意接受组织的特殊关照。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只是在家人的搀扶下,乘坐了这辆专车,轻轻转了几圈,以示已领略了国家给予的待遇。随后,他主动请组织将专车投入到工作中,分配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中央倾注了所有力量,却终究未能挽留邓稼先的生命。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突发全身大出血而离世,享年62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遗言仍旧是:“切莫让我们落后于人……”在他离世13年后的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再次追授给他一枚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付融宝配资,配资世家炒股配资开户,配资点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